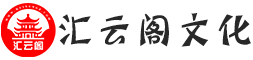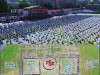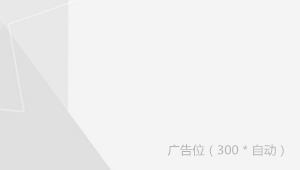当IP改编的海潮退去狂热的泡沫,近期播出的《藏海传》与《长安的荔枝》如同两颗棱角分明的石子,在古装剧创作的湖面激起层层荡漾。两部剧集都在原著底子上举行了大胆改编,摆脱了对IP的路径依靠,在内容原创性上迈出新的一步。剧情观照实际,与当下的观众形成猛烈的感情共振。但在人物塑造、叙事打磨和传统文化元素的利用上也碰到了新的逆境。


原创性改编观照实际
《藏海传》脱胎于南派三叔《盗墓条记》的支线《藏海戏麟》,仅依据原作者在微博上发表的几段散碎笔墨,联合“洪武年间”的配景、“汪藏海组建神木司”“汪藏海精于风水堪舆、营造修建”等元素,就以汪藏海为原型塑造剧作主人公藏海,并构建起40集完备的叙事体系;《长安的荔枝》则以马伯庸七万字的同名中篇小说为蓝本,围绕“一骑尘世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睁开想象,以荔枝转运这一微观变乱切入,用35集的长剧体量描绘出唐朝官场与民间的百态图。
两部剧均突破了原著限定,实现了将小故事改编为长剧集的突破。
在改编处置惩罚上,二者各有千秋。《藏海传》中,藏海的家国故事、权术结构均为原创内容,乃至焦点道具“癸玺”的争取逻辑也跳出了原小说的盗墓框架,形成了完全独立于原著之外的叙事体系,是一种从“文本碎片”到“完备脚本”的原创模式。而《长安的荔枝》则是以原著小说为骨,接纳“短文改长剧”的创作模式,通过新增脚色、添加故事线、强化谐趣风格、增补汗青细节等方式,使内容更为血肉丰满。
在叙事上,两部剧集显现出差别的节奏计谋和关注层面。《藏海传》以高密度的智谋比武推动剧情发展,首集便交接了主人公藏海的宿世此生,之后敏捷睁开“修筑王陵”“棋子殉葬”等高能情节,将藏海背后盘根错节的权术暗黑之网渐渐撕开。这种快节奏叙事精准贴合了Z世代(指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也被称为“网生代”“二次元世代”)观众的独特审美意见意义。
在满意年轻观众娱乐需求的同时,怎样观照实际表达,剧集也做了不少创新实验。《藏海传》颇具巧思地借剧情发展隐喻当代职场生态:从初入侯府时的小心翼翼,到另立流派时的斗志昂扬;从平津侯府的暗流涌动,到钦天监的波谲云诡——藏海在提升之路上履历的种种,被网友总结为“今世职场生存指南”。正是这种与观众告竣的感情共振,让该剧得以爆红。
相比于《藏海传》的快节奏叙事,《长安的荔枝》则以慢节奏叙事为古装剧扩容。相较于原著小说,剧集更加细化地出现了李善德成为荔枝使的缘由,显现了大唐“打工人”李善德在长安贷款买房、遭遇同侪倾轧、被动卷入权术斗争等遭遇。剧集同样将盛唐的官场与今世的职场精密关联:李善德掉入同侪经心计划的捧杀陷阱,接下荔枝使的使命,不得不远赴岭南寻求一线生气,却在使命推进过程中遭遇各部分的推诿扯皮……当代职场中存在的“甩锅文化”“流程壁垒”等积弊被具象化为荔枝转运过程中,李善德眼前一座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而李善德被封建官僚体系“异化”,又终极与之决裂的过程,则显现出个体面临巨大外部体系裹挟时的挣扎与觉醒。令人感慨的是,那些曾经拦阻荔枝转运的繁文缛节与官僚之间的权利倾轧,终极都随着安史之乱的到来,化作盛世崩塌前的可笑注脚。
剧集靠近尾声处,李善德以外貌奇怪、实则腐烂的荔枝圆满交差,在劈面痛斥右相杨国忠后金蝉脱壳,并借此让圣上处罚了鱼承恩等奸佞之臣,完成了这一人物从“职场老黄牛”到“体制苏醒者”的蜕变。这些情节固然多少带有抱负主义色彩,却通过以史鉴今的方式,精准击中了今世观众的感情痛点,显现了古代小人物的巨大与悲壮。《长安的荔枝》完成的不但是李善德个人运气的誊写与重塑,更有对旧时封建官僚贪腐成性、尸位素餐、鱼肉百姓的深刻批驳。
二者相较,《藏海传》更偏重个人发展与权利博弈的戏剧化出现,而《长安的荔枝》更具社会批驳意识,二者共同拓展了古装剧在观照实际维度上的大概性。这种古今映照的叙事计谋,既保持了汗青剧的质感,又赋予了作品猛烈的实际指涉,使观众在欣赏古代权术戏码的同时,也得到不少职场启示与感情代价。
主角光环减弱了表达深度
作为古装剧的范例突围之作,《长安的荔枝》和《藏海传》却在“范例创新”与“实际深度”的抵牾中遭遇新的逆境。两部剧集固然都有冲破通例的叙事野心,却缺乏踏实的情节计划举行支持,偶然只能依仗主角光环的加持来推进剧情发展,并在叙事逻辑上存在不敷和“硬伤”,从而减弱了剧集表达的深度。
以《长安的荔枝》为例,在原著小说中,李善德荔枝转运的举措,旨在体现唐代底层官吏在体制重压下的生存博弈,以及主人公的聪明与实际逆境之间形成的戏剧张力。剧集改编却陷入主人公“动机简化”与“光环加身”的双重困局:一方面,李善德誓要完成荔枝转运使命的动机,被压缩成只是为了保全女儿的单一情绪驱动,淘汰了他在原著中“为生存而算计”的人物复杂性;另一方面,强行插入李善德与荔枝园的侗族女孩阿僮、胡人商会头目阿弥塔的情绪线,这些跳脱实际逻辑、似有还无的情绪戏码,不但让李善德的智谋、积极被稀释,更有将女性脚色简化成给“主角光环”做注的工具人之嫌。
《藏海传》同样陷入了此类创作窠臼。主人公藏海的复仇与心田挣扎本应成为剧情深入出现的内核,可以就此深入发掘权利漩涡中人性的复杂与幽微。然而遗憾的是,全剧并未能通过有用的叙事充实展现藏海复仇的深层意义。一些剧情设定也缺乏逻辑动因,如藏海以幕僚身份搅动朝局的设定就缺乏公道的剧情做铺垫,让人无法佩服。其发挥权术所仰仗的纵横之术与堪舆武艺,也始终游离于霸术博弈的焦点之外。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这些本应表现在权术比力上的“杀手锏”,终极沦为了“金手指”式的叙事捷径,难以触及权术斗争的深层逻辑。
叙事视角的杂乱和叙事逻辑的单薄也值得留意。《长安的荔枝》中岭南部门的剧情,重心一度偏移至郑安全与何刺史的“兵符闹剧”,而此时主角李善德完全沦为配景板,其运送荔枝的焦点举措被简化为与贩子的斡旋,致使全剧的权术叙事沦为插科讥笑的笑料,而本应突出显现的主人公面临运气危急时的茫然和在民间情谊加持下重获盼望的曲折过程,却被“抢戏”了。
剧集还出现了不少“降智桥段”与“逻辑硬伤”:开篇,郑安全忽然就被左相选中,作为心腹去偷听杀人,被网友责怪逻辑不通、过于儿戏。大了局处,假如说郑安全为救李善德父女而身死,尚可明白为通过“笑剧转悲剧”的伎俩完成脚色的升华,那么小厮狗儿拔刀殉主,化为灵魂后与郑安全的灵魂相见,还哭喊着“我怕天上没人奉养你”,则太过离开实际,强行煽情。而这对人物的了局设定,也不外是为给李善德携女隐居岭南的“圆满”强行铺路。要知道,一方面,以郑安全的武力值就撤除了白望人头目并不能让人佩服;另一方面,右相及其麾下党羽怎么大概让李善德容易就逃走了追杀呢?
而《藏海传》中,平津侯、庄之行、瞿蛟等反派脚色被塑造得过于扁平化,反派庄芦隐对藏海“百依百顺”到了令人费解的田地。庄之行从追查生母死因的复仇者,蓦地变化为弑父夺权的叛逆者,其关键的生理嬗变过程也被“藏海答应扶持”的简朴缘故原由急忙带过,袒露出次要脚色在剧情推进中被工具化的范围。权术斗争也因主角太过“高光”而沦为缺乏智力博弈的外貌辩论,复杂的政治角力也简化为“主角开天眼”的剧情游戏。
更值得商讨的是,剧集将“癸玺”“瘖兵”等盗墓元素强行嵌入权术框架,这种嫁接不但未能丰富叙事条理,反而将剧集拉入盗墓寻宝题材的套路。主人公的复仇动机被锚定在“为亲情复仇”与“探求癸玺”上,让人物缺失了实际深度,也没能跳出主角光环加持下的爽剧模式。
这种创作倾向也在某种水平上反映出当下古装剧广泛存在的逆境:权术斗争沦为外貌文章,叙事逻辑让位于即时快感。这种改编,既背离了原著见微知著的深刻汗青洞察,也让剧中人物在“次要脚色工具人”与“主角光环持有者”之间失去锚点,导致剧集与原著的实际主义深度相去甚远。《长安的荔枝》与《藏海传》若想突破困局,其改编就不应仅停顿在对实际的悬浮疏离与对汗青的戏谑解构之上,而应对权术博弈与民气比力有更真实、更深刻的洞见。
传统文化符号难与叙事深度融合
在古装剧市场竞争白热化、创作伎俩趋于模式化的配景下,《长安的荔枝》和《藏海传》在视听语言的运用上,都显现出探索的前锋意识。两部剧都注意将东方美学元素与视听语言举行积极融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影像风格。
以《长安的荔枝》为例,剧中以书信作为情绪载体,李善德与女儿的尺牍往来,不但是舐犊情深的具象化表征,更通过极具东方美学意蕴的空镜头,将笔墨转化为视听意象——当岭南的荔枝与长安的家书在镜头中交织剪辑,书信逾越了通报信息的载体功能,成为封建官僚体制重压下个体情绪的表达与依托。这种将一样平常生存符号诗意化的镜头处置惩罚,赋予了“家书”新的美学意义。
《长安的荔枝》还特殊在每一集的片头插入风格化的人物前史,并融入不少传统文化元素。如第32集片头的《孔雀翎》就以泉州非遗文化木偶戏的演出情势,报告了一个少年与羊的故事,在交接胡商苏老配景与其为人的同时,也暗示了他与李善德的交情将走向破碎。
《藏海传》中也融入了不少传统文化元素。在人物对决的场景中,昆曲水磨调的婉转声腔与麋集铿锵的鼓点节奏形成听觉对冲,增强了戏剧张力;在藏国内心独白时,非遗皮影戏的动态剪影奇妙地将人物的复仇欲望外化,并通过老虎、蜈蚣、老鹰等视听意象带给观众更直观的“兽性围猎”之感。别的,镜头通过叠化技法实现实际与幻觉的无缝转场,加之留白处的精妙音效,使这部剧在视听语言的表达上,颇有蕴藉隽永的东方美学之韵。
固然在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与化用上,两部剧都显现出差别向度的艺术巧思,但在将传统文化符号打造为真正的情节齿轮,为推动叙事服务方面,两部剧也都袒露出显着不敷。
在《长安的荔枝》中,何刺史着迷斗鸡、喜好鸡宝,并为战死的斗鸡举行葬礼等情节,在视听语言上是将斗鸡品德化,共同燃爆的配景音乐,雨中格斗的局面被处置惩罚得颇有燃点。通过游戏化和戏谑化的场景将剧情表达的怪诞性拉伸至极致,为观众提供了不少笑料。遗憾的是,剧集并未能将斗鸡场景与官场博弈形成更深层的意象勾连,只停顿在了视听层面的新颖与炫技。
《藏海传》中,传统文化元素也没能真正嵌入叙事肌理。主创虽故意将“封禅台风水破局”“沈楼构造陷阱”等场景与堪舆之术、天道玄学举行深度绑定,但是对于相干元素的运用却只停顿在人物“破局—制胜”的表层叙事,未能从更深层面将其融入剧情计划。而藏海拆解榫卯布局的一场戏,极具象征意味,本可延伸出对民气叵测或天地调和的哲学式思索,却因缺乏后续的意象追踪而流于情势。这种传统文化元素运用与剧情内在构建上的割裂,使传统文化元素的化用陷入了“形至而神不至”的逆境,带给观众“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
《长安的荔枝》和《藏海传》两部剧集折射出当下古装剧的创作转型之势。在题材融合层面,它们突破宫斗、武侠等传统叙事范例,告别古今元素的简朴拼贴,以更加丰富多元的视角,将职场规则、家庭伦理、女性意识等当代议题嵌入汗青语境,使古装剧真正成为今世社会的“汗青棱镜”。但同时,剧集也袒露出古装剧在叙事打磨与人物塑造上不敷。
大概,只有回归“人物为本、情绪为基”的实际主义创作初心,让主角光环服务于叙事逻辑,让权术斗争扎根于实际泥土,古装剧才气从娱乐载体“升格”为文明对话的场域,在汗青的褶皱中触摸真实的温度,听到实际的反响,誊写出更具深度的期间寓言。